题记:
民间留念,黄土地上的歌谣。
劳动或者人民
(组诗) 闫秀娟
熏 枣
几孔老窑洞
一个土坡坡
一堆一堆红枣
一口大铁锅
腾腾往上冒热气
谁也不说话
我们在热气这边
干活儿的老人和小媳妇
在热气那边
老人很老
小媳妇很年轻
都很卖力气
我们看了那么久
也没看出来他们
是不是父女
坡坡上卧一只狗狗
一边有一个小孩
说熏枣的是爷爷和妈妈
边上抽烟的是奶奶
奶奶头上有个火罐印
披一件外套
穿一条旧牛仔裤
我们问奶奶是不是有病了
女孩说没病
说奶奶半夜四点就起来做饭
来了一辆三轮车
又拉来一车枣
俩个孩子追上叫爸爸
奶奶过来了
奶奶和爸爸一袋子一袋子
把红枣往大锅跟前抱
我问他们家
是不是可有钱了
姐姐说没有
弟弟说有了
说他有了
姐姐就跟上我们笑
狗狗就直摇尾巴
你 好
你好师傅
看见一个手包没有
师傅拿着扫帚
打量着我们说没看见
车里人还在说
说小偷怎么怎么
师傅知道怎么回事了
说以后一下车
要记着把车门闭上
车里人没说话
看着这个环卫女工
环卫工又说
以后让放羊的齐放格
不要让打麻将的打了
打麻将打得人就完了
环卫工眼睛圆圆的
说得一本正经
接着又说了一遍
说让放羊的齐放格
说我们连羊肉也吃不上
她谁也不看
就走就和我们说话
还是一本正经
她把放羊的打麻将的
和我们和社会
都放在了一起
我们想着她说的话
看着她的环卫服
看着她那扫帚
一下一下一下
不知要扫到什么时候
那说话的口气和眼神
让我们和小偷
和放羊的打麻将的
和所谓的思想斗争了一路
又过了几天
我们迎面碰上
我笑了一下
她也给我笑了一下
就像一个乡下姐妹
就像她什么也没说
真 的
十五个人的垃圾场
一样的口罩 手套 雨靴
一样的工作服
不说谁也看不出
看不出他在最前边
在最危险的中心区域
在沼气管道之间
看不出这个搞臭专家
把手挡在鼻孔前
一遍遍闻沼气
闻气体走向动态
掌握流量和成分
一个一个管道口
一个一个过滤处
不同的区域
十五个人
少了谁也不行
看不出
一天近三百吨垃圾
四五十台垃圾车装载机
流水运转
大面积填埋
看不出这垃圾处理场
究竟有多臭
有多少飞蝇臭虫
追赶着沼气和汗水
追赶着他们的意志品质
精神和物质
追赶着
劳动和人民
仿佛只剩下分秒
只剩下洗也不掉的臭味
只剩下十几个人
蹲在院子里吃饭
一个离一个远远的
谁也不说话
只剩下他
还在垃圾处理场
来了一个电话
问他哪里了
他说垃圾场
人家就把电话挂了
他知道朋友想叫他吃饭
又是嫌他脏了
他自己也嫌自己脏了
只剩下他坐垃圾车进
坐垃圾车出
只剩下这个当厂长的
还和孩子和环卫工老婆
住在公厕里
就和住在家里一样
只剩下他们俩口子
几年没买一件新衣服
只剩下
手是垃圾的
鼻子是沼气的
只剩下
这条路是社会主义的
心是国字号的
只剩下他衣兜里
常装的《党章》
真的,就是《党章》
他说 不为什么
就为哪时学哪时方便
说得可认真了
谁也不觉得
那是装出来的
心 在 弦 上
他就坐在沙发扶手上
弹着唱着
绑在小腿上的快板很快很响很亮
他使不完的气力
在青筋鼓胀的脖子上
在随音调拧扭的肢体上
他说不完的话
在心上在三根弦上
在很远的地方
在他曾用渠树钢丝葫芦做的板胡上
在他用过的那七八套快板
四把三弦五把二胡两把板胡上
他弹着唱着
唱他十六岁跟上道情班子
挣来三块两块钱交给爹娘
唱他二十二岁去黄河天桥水电站
当了八年民工连长
唱他三十二岁没了老婆
丢下三岁四岁六岁三个孩子
唱她那年娶了十八岁的张花兰
唱张花兰听他说书听着听着就会了
唱他睡梦中唱着唱着就把自己唱醒了
唱他把生字写在手背上
一个字一个字都问会了
他就唱着弹着
把自己的七十多年
唱成了夕阳
他唱得满面红光眼睛泛亮
声音和皱纹长在了一起
和张花兰和民间长在了一起
他弹着唱着
晃着脑袋和身子
感觉声音是在他的土地里
在白羊肚里
在每一个骨节缝里
在每一个毛孔里
长出来的
简 历
任宏民,男
一九一八年出生
某年某月某日
在只有三孔窑洞的公社里
第一批宣誓入党
他唱共产党爱穷人
天下穷人心连心
三十岁当队长
和社员们治沙开荒
月亮地里
推木轮车打坝造田
红旗插上高圪堵
三十六岁参加榆林农运会
背三十斤明沙
光着大脚跑一万米
跑了第一
奖了紫花花被面子
一九五九年大会战
白天修打坝梁水库
晚上收庄户
领着十几个人
把老婆积攒的
一罐子萝卜缨缨咸菜
和玉米糁糁
一顿吃了个净光
一路挖渠修桥修大路
从瑶镇高家堡神木
一路当劳模
当到榆林
雨靴是奖的
茶缸子是奖的
挖东干渠的铁锨
也是奖的
某年某月某日
吹完出工号
到地里天还没亮
自己先背了一垛黑豆
脱了鞋过沤泥滩
踩着冰凌子
跳水壕没跳过去
黑豆垛压在身上
窝住了脖子
社员们分头找他
卸下垛子才把人救上来
就这么歪着脖子撇着腿
还把垛子背回村
县上开三干会
菜吃饱了
回来揣两个馍馍
给村里孩子一人尝一口
说穷不留根
再穷也不能哭鼻子
要早早起了要忙了
五十二岁胃病
五十四岁去世
走的时候还是歪脖子
走的时候
放不下一男七女
(组诗) 闫秀娟
熏 枣
几孔老窑洞
一个土坡坡
一堆一堆红枣
一口大铁锅
腾腾往上冒热气
谁也不说话
我们在热气这边
干活儿的老人和小媳妇
在热气那边
老人很老
小媳妇很年轻
都很卖力气
我们看了那么久
也没看出来他们
是不是父女
坡坡上卧一只狗狗
一边有一个小孩
说熏枣的是爷爷和妈妈
边上抽烟的是奶奶
奶奶头上有个火罐印
披一件外套
穿一条旧牛仔裤
我们问奶奶是不是有病了
女孩说没病
说奶奶半夜四点就起来做饭
来了一辆三轮车
又拉来一车枣
俩个孩子追上叫爸爸
奶奶过来了
奶奶和爸爸一袋子一袋子
把红枣往大锅跟前抱
我问他们家
是不是可有钱了
姐姐说没有
弟弟说有了
说他有了
姐姐就跟上我们笑
狗狗就直摇尾巴
你 好
你好师傅
看见一个手包没有
师傅拿着扫帚
打量着我们说没看见
车里人还在说
说小偷怎么怎么
师傅知道怎么回事了
说以后一下车
要记着把车门闭上
车里人没说话
看着这个环卫女工
环卫工又说
以后让放羊的齐放格
不要让打麻将的打了
打麻将打得人就完了
环卫工眼睛圆圆的
说得一本正经
接着又说了一遍
说让放羊的齐放格
说我们连羊肉也吃不上
她谁也不看
就走就和我们说话
还是一本正经
她把放羊的打麻将的
和我们和社会
都放在了一起
我们想着她说的话
看着她的环卫服
看着她那扫帚
一下一下一下
不知要扫到什么时候
那说话的口气和眼神
让我们和小偷
和放羊的打麻将的
和所谓的思想斗争了一路
又过了几天
我们迎面碰上
我笑了一下
她也给我笑了一下
就像一个乡下姐妹
就像她什么也没说
真 的
十五个人的垃圾场
一样的口罩 手套 雨靴
一样的工作服
不说谁也看不出
看不出他在最前边
在最危险的中心区域
在沼气管道之间
看不出这个搞臭专家
把手挡在鼻孔前
一遍遍闻沼气
闻气体走向动态
掌握流量和成分
一个一个管道口
一个一个过滤处
不同的区域
十五个人
少了谁也不行
看不出
一天近三百吨垃圾
四五十台垃圾车装载机
流水运转
大面积填埋
看不出这垃圾处理场
究竟有多臭
有多少飞蝇臭虫
追赶着沼气和汗水
追赶着他们的意志品质
精神和物质
追赶着
劳动和人民
仿佛只剩下分秒
只剩下洗也不掉的臭味
只剩下十几个人
蹲在院子里吃饭
一个离一个远远的
谁也不说话
只剩下他
还在垃圾处理场
来了一个电话
问他哪里了
他说垃圾场
人家就把电话挂了
他知道朋友想叫他吃饭
又是嫌他脏了
他自己也嫌自己脏了
只剩下他坐垃圾车进
坐垃圾车出
只剩下这个当厂长的
还和孩子和环卫工老婆
住在公厕里
就和住在家里一样
只剩下他们俩口子
几年没买一件新衣服
只剩下
手是垃圾的
鼻子是沼气的
只剩下
这条路是社会主义的
心是国字号的
只剩下他衣兜里
常装的《党章》
真的,就是《党章》
他说 不为什么
就为哪时学哪时方便
说得可认真了
谁也不觉得
那是装出来的
心 在 弦 上
他就坐在沙发扶手上
弹着唱着
绑在小腿上的快板很快很响很亮
他使不完的气力
在青筋鼓胀的脖子上
在随音调拧扭的肢体上
他说不完的话
在心上在三根弦上
在很远的地方
在他曾用渠树钢丝葫芦做的板胡上
在他用过的那七八套快板
四把三弦五把二胡两把板胡上
他弹着唱着
唱他十六岁跟上道情班子
挣来三块两块钱交给爹娘
唱他二十二岁去黄河天桥水电站
当了八年民工连长
唱他三十二岁没了老婆
丢下三岁四岁六岁三个孩子
唱她那年娶了十八岁的张花兰
唱张花兰听他说书听着听着就会了
唱他睡梦中唱着唱着就把自己唱醒了
唱他把生字写在手背上
一个字一个字都问会了
他就唱着弹着
把自己的七十多年
唱成了夕阳
他唱得满面红光眼睛泛亮
声音和皱纹长在了一起
和张花兰和民间长在了一起
他弹着唱着
晃着脑袋和身子
感觉声音是在他的土地里
在白羊肚里
在每一个骨节缝里
在每一个毛孔里
长出来的
简 历
任宏民,男
一九一八年出生
某年某月某日
在只有三孔窑洞的公社里
第一批宣誓入党
他唱共产党爱穷人
天下穷人心连心
三十岁当队长
和社员们治沙开荒
月亮地里
推木轮车打坝造田
红旗插上高圪堵
三十六岁参加榆林农运会
背三十斤明沙
光着大脚跑一万米
跑了第一
奖了紫花花被面子
一九五九年大会战
白天修打坝梁水库
晚上收庄户
领着十几个人
把老婆积攒的
一罐子萝卜缨缨咸菜
和玉米糁糁
一顿吃了个净光
一路挖渠修桥修大路
从瑶镇高家堡神木
一路当劳模
当到榆林
雨靴是奖的
茶缸子是奖的
挖东干渠的铁锨
也是奖的
某年某月某日
吹完出工号
到地里天还没亮
自己先背了一垛黑豆
脱了鞋过沤泥滩
踩着冰凌子
跳水壕没跳过去
黑豆垛压在身上
窝住了脖子
社员们分头找他
卸下垛子才把人救上来
就这么歪着脖子撇着腿
还把垛子背回村
县上开三干会
菜吃饱了
回来揣两个馍馍
给村里孩子一人尝一口
说穷不留根
再穷也不能哭鼻子
要早早起了要忙了
五十二岁胃病
五十四岁去世
走的时候还是歪脖子
走的时候
放不下一男七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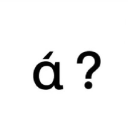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